我寄人间雪满头
初识钱钟书先生,是《围城》中。城里的人想出来,城外的人想进去,熙熙攘攘,多不如愿。阖书,闭眼,顿觉作者仿若过客,冷眼旁观这世态纷扰。本人只坐拥一壶茶,一支墨笔,一帘孤灯,在光影圈出的世界里静静看着,随手书就,便是一片方圆。
在《洗澡》中邂逅杨绛先生。那时尚不明白:为何一介闺秀,却被大家尊称以“先生”?这问题很快被抛诸脑后,取而代之的是那字里行间的刀光剑影,过往云烟。那时觉得先生大抵是接过了一盏热茶,在老北京喧闹的茶馆里,慢慢讲。
那多年以后,“钱钟书”与“杨绛”,这两个名字就像孤独的符号般,存储在记忆里。符号的背后代表的意义深重厚远,符号之间却一片空白,再无半分联系。直到那日有拜读了《我们仨》,方惊觉自己认知之浅陋粗鄙。过往的字符分居两地,即便厚重,也无端添了几分单薄。而今恍然惊悟,才知那之间一直连着一条红线,一端是彼此的名字,另一端连的,是“家”。
杨绛先生在书里这样说:“三里河的窝所,曾是我的家。因为有我们仨,我们仨失散了,家就没有了。”这段话就这样突兀地击中了我,一时间笔墨里承载的厚重与温暖铺天盖地压了过来,直压得自己弯腰、屈膝,不察间已是泪流满面。是的,他们可以甘于平淡,可以不畏苦难;可以朴素、可以平凡;他们不过是夜间万家灯火的一点,但等到彼此手牵手相携走完,步履在泥泞的岁月里落下一行行脚印时,所有的平凡却又都变作不凡。那段在峥嵘岁月里相互扶持的记忆,便在泥窝中一闪一闪,发着光亮。只因有我们仨。
“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挥笔至此,不知谁又在黑夜里发出一声喟叹。我随杨绛先生的记忆走过去,溯着时间的浪潮,直走到一个夏日的牛津。那时两人方结婚,一同至此求学。我看见许多琐琐碎碎的小事:早饭、晚饭间的散步,他们一同“探险”;牛津大学图书馆里一个人摊开书静静看着,光阴为他铺下一片风景;钟书“笨手笨脚”,杨绛就安慰他,一面对着损毁的家具头疼,一面说着:“我会修”……就是这样平淡温馨的小事,却令人温暖伤感地想要落下泪来。
最记得那一段:钟书要前往北京开会,古驿道杨柳依依。没有长亭复短亭,却有杨绛先生一路追着,循客栈而来;水虽静而不止,钟书先生在船上,随水不停流去;杨绛先生一面宽慰重病在身的女儿,一面跌跌撞撞往前走。
想来那时应当有钟声,“当——当——当——”寂静、庄严、厚重。钟声厚重,重到盖过一切红尘里浮华纷扰;钟声亦轻灵,轻灵地漾开身边烦杂。偌大的世界里只有两个人走走停停的背影——或许还要加上女儿倾吐一天见闻的欢声笑语,他们在钟声里走远,夕阳为彼此刻下最缱绻的侧影。
他们本是平凡,却因长久相伴而真情缠绵,情爱相依。若火冶剑,如水淬金,所有的平凡在回顾时都已变了不凡。丈夫与女儿走了以后,杨绛先生在积病里写下这本书,聊以慰藉。人在书里,我在书外,两者做的是同一场人间大梦。梦醒了,四下白茫茫只余我一人;于是,沉睡的感官一同苏醒,有我在书外,于层层叠叠的梦境交织的幻影中,痛哭失声。
——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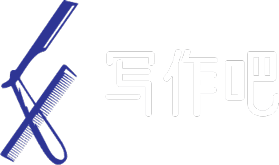
暂无评论
发表评论 我再想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