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终于出逃,逃回山河大地 ——读《文化苦旅》有感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两者关系如何?”
“没有两者。路,就是书。”
这是余秋雨先生在《文化苦旅》一书中提到的一组问答。
作为地地道道的“山河之子”,作者在被书本推进城市后,选择的仍是“出逃,逃回山河大地”。这是我初读时所迷惑的:究竟为何,这对山河深深的眷恋究竟来自何处?
在书中,我看着作者到了都江堰,漏空的索桥、冷气砭肤的江流,由惊讶到惊叹,望着近旁的青城山,最后竟悟着了“道之道,也就是水之道,天之道,生之道,也是李冰之道、都江堰之道”;作者到了天一阁,“剥除斯文,剥除悠闲,脱下鞋子,卑躬屈膝,哆哆嗦嗦,恭敬朝拜”,久经风雨的藏书阁此刻进行着一场安静而纯粹的朝拜仪式;作者在上京龙泉府,望着废井冷眼,昔日渤海国的盛衰在脑海中一次次回荡……
这些都是作者在逃回山河大地后所发现的。或许不同于如今的人们为了逃离城市的嘈杂而前往乡村放松自我,作者始终把继承山河文化当做自己不可推卸的使命,是使命,亦是一份热爱。
我们可以很轻易的说自己“喜爱山河”,可这“喜爱山河”又怎是一张张山河前的合影所能表达的呢?再清晰的照片,留下的只是山河一瞬的姿态。而那亘古的山河文化在我们转身离去后,可能就与我们无缘了。自古文人好游山玩水,如今的我们依葫芦画瓢,却鲜有人能再写出真正属于山河的文章,是我们逐渐失去了对山河的那份深沉的爱吗?
人和山河生来就是一组对比吧,山河是沉默的,相比起来,人就如莽撞的青春期。人们在山河旁叫嚷着,肆意地宣布“人类是生物链的顶端”,山河在一旁无言,就像父母看着胡闹的孩子,担忧却也有些无奈。有一天,人们突然发现罗布泊消逝、月牙泉水位下降,人们开始着急,这时的山河依旧沉默,眼中添了几抹忧伤。
人,脆弱如苇草……
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
庸碌一生,人纵使活了百年,充其量仅算山河在历史长流中不经意的一瞥。我曾想,山河如果有记忆,在某一个瞬间瞥到了人,它们是否会记下这些人?在寂寞的岁月里,它们是否会想起那些陪伴自己一小会儿的人呢?
我猜,它们是会的,山河亦是有情的。每当我们轻声唤到“山河”时,可能会有轻声的应和,来自遥远的山河,也来自我们内心深处。
无论我们在与不在,山河就在那里,静默而又深情。
无论山河在哪里,山河文化始终流淌在我们的血液里。
“千般荒凉,以此为梦;万里蹀躞,以此为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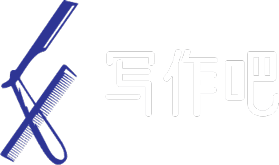
暂无评论
发表评论 我再想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