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读《苏东坡传》后感
这一生,他只是永恒在刹那间闪现的一个微粒,他究竟是哪一个微粒,又何关乎重要?所以生命毕竟是不朽的,美好的,所以他尽情享受人生。——林语堂
仲春的苏堤,犹如一条翠色的丝缎,堤桥相连,南接南屏,北聚栖霞岭,一湖的澄碧漫卷开来,翠绿氤氲如靄的岸上,婀娜细柳,枝叶低垂,剪一隙骄阳碎光,袅娜柔情似湖水。
沐雨坐于一苏杭酒楼,望前堂东坡雕像。这座江南古城,与苏子情怀难舍难分。垂眸瞰彼岸,一座夫子庙,牌匾上烫金的大字已斑驳,圆柱华美的朱漆亦不经淫雨霏霏,凋谢了容颜。
静女其姝,自牧归荑。如今夫子庙前又有谁曾挽起朱巾翠袖,拾起白芷芳汀?孔子,苏轼,一个在群雄并起的东周苦推周礼,一个生在国力渐衰的北宋中末,贬谪于各地,颇似孔夫子“周游列国”。他们何其相似,又何其不像,都生不逢时,政途坎坷;都广博多才,胸襟广远;不过一个弟子三千,终吟着那“太山坏乎!梁柱催乎!哲人萎乎!”的绝命诗,带着雄心饮恨而尽。一个佳作流芳,终带着对佛学的虔诚,在方丈超度下,在南方常州平静地走完生命的最后一程。
读了大师林语堂的《苏东坡传》,才知道苏子原来信佛。生命中仕途失意的缺憾未能使他消沉,政治理想未能承载之重量,使中华史上少了一名噪一时的为政者,而多了一个伟大的灵魂。他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卓越的书法家,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甚至是酿酒实验者,他对生命白纸上的黑点,不是抹除,不是遮掩,而是将它渲染成更为多彩的水墨画卷。
宋王朝,一个积贫积弱,偃武扬文的王朝,一个北狄入侵,小人当权的时代。王安石变法,经济上垄断专卖,苛捐杂税,抑制民间资本主义萌芽。政治上打压元老重臣,任人唯亲,只为穷兵黩武,为北方战事的胜利陷民于水火。欧阳修、韩琦、司马光均或辞官回乡或遭贬谪迫害。独苏轼,被贬前敢用科举考题抨击变法弊端,贬后敢上万言书直抒胸臆;为政地方,兴修水利,鼓励经营,坚持尽一己之力抵制变法的偏执。他不曾忘记,始终惦记着日趋衰落的国运;他乐与百姓为友,心系黎庶疾苦;他代表着社会的良知,王朝的气数。随着以苏子为代表的一代良臣退去,日渐凋零。他逝世后二十五载,靖康之变,浮萍般北宋一朝雨打风吹去。
贬谪于各地,黄州、杭州,乃至海南岛,可谓“白头来往人间遍”。年轻时却有“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的惆怅,而其后,岁月沉淀的智慧使他很快学会了包容。他包容当权者的迫害,包容故友的背叛,入乡随俗,他总能吸取一方文化的精粹,对佛学的信仰,也在起起落落的贬谪岁月中扎根于心,域外茫茫海南岛,蛮夷之地,他仍以包容一切的乐观,包容南境瘴气,甚至能与渔樵为伴,能亲赴山野采药。恕人,亦是恕己,珍惜生命,不将岁月付于怨天尤人,不将心境毁于仇恨愤嫉,纵使不能得己所欲,也爱己所得。古往今来,无数人或苦于失意,或哀于寂寥,或困于情痴,读《苏东坡传》后,才知真正广博的心灵是包容自己——包容自己的失意、寂寥、情痴。
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余怀,望美人兮天一方。返璞归真,活出生命最美的姿态,包容自己,方能接受世界。
苏子重情,以诚待人,他能强烈地爱,也能强烈地恨,而他总能在二者中总选择前者。欧阳修、张方平、佛印禅师、弟弟苏澈……。他的人生中从不缺挚友,总能寻那一人得到灵魂与精神世界的共鸣。王弗、王闰之、朝云,前后三位妻子,与他并无“人生若只如初见”的缠绵,没有“为伊消得人憔悴”的痴心,却能在平凡的生活,多舛的时运中相濡以沫,成为贬谪时日中彼此的守望与慰藉。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料的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岗。那月色皎洁温柔如水,月下人形单影只。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斯人已逝。月亮于苏子,宛若一位故友。“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又如那“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二人者耳”的追问,“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守望。每仰望星空中那一轮明月,徐徐清辉,必能涤荡诗人心上柔软的一角。月静,心殇。
六十四岁,哲人人生走到了尽头。面对方丈,“现在,要想来生”的宽慰,苏子只答“勉强想就错了”。弟子曾问孔夫子,贤人将死,有无怨恨?夫子只答“求仁而得仁,又有何怨?”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我们不信宗教,更不信来生,可无论孔子还是苏子,均尽此一生坚定地践行了自己的人生价值,人终已去,其思想智慧则流传于今,经久不褪。至于来生,或也只是他们通向另一个世界时,一个幽远的回眸罢了。
烟雨,西湖。已近傍晚,空气裹挟着漉漉的雨滴,暮霭临湖,忆那《苏东坡传》,呷一口清茶,心头,骤暖。时至今日,千年已过,或许无人能说清苏子的眉目,而大师林语堂却用文字,摹出了一个超脱于时空之外的灵魂。
大师说苏子,又何尝不是隔着千年,寻着自己心翼上的一丝慉颤?他一定也从这段旖旎的人生中读出了自己的影子吧。孔夫子、苏子、林语堂,世事变迁,中华传统道义文化的精粹,却根植于每一位中国吾子的精神家园中,构成了中国知识分子品质最优秀的部分。
下楼,撑一把油纸伞,行湖畔,夜几乎已透黑,竟恍惚见一身影,亭亭立于湖岸的芦苇丛中,近了,那影已远了,只听那风声似飒飒吟着。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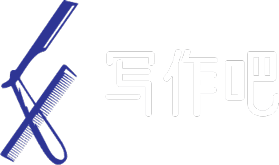
暂无评论
发表评论 我再想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