冥想中的精神跋涉 —— 读《我与地坛》有感
人生如投逆旅,是一个不断经受苦难的过程,唯有超越世俗的真诚信仰,才是渺小的生命的福祉。
摊开一本蓝底白花的史铁生精选集,不禁为史铁生的文字所叹服:它们忽而遥远,遥远得如同宇宙洪荒中的一粒尘沙;忽而亲近,亲近得就像茶盏中飘散的缕缕清香。其中一篇散文《我与地坛》,尤其令我感触颇深。
地坛——安放灵魂的归宿
正如作者自己所说,“在活到最狂妄的年龄忽地残废了双腿”,是一次致命的打击,足以令人魂飞魄散。命定似的,他来到地坛,而地坛历经沧桑四百多年,也只为这一刻的相遇;命定似的,他要在这里痛苦地思索,艰难地开辟出一条救赎灵魂的路。他曾经一次次地问自己,“我为什么要活着?我要怎样活下去?”于是,这个时候,他总能感知到那荒芜却并不衰败的园子里,有群燕的高歌、有古殿檐头的风铃响、有爬满青苔的石阶、还有瓢虫在嬉闹。于是,他整日整夜地待在园子里。这样好几年,他告诉自己:死亡是一个必然降临的节日,那为什么不试着活下去。于是,他开始写作,苦苦等待一个黎明。
我常常想,在人口密集的城市里,苦难的人们往往需要这样一个宁静的地方来安放灵魂。我曾把某一个地方视为乐土,身在其中,会猛地想起湮灭许久的往事,忆起许多故人的音容笑貌。就好像是一种溶剂,溶化了尘封 的 盖 子,如烟的温情就升腾出来了。如今,人们在单调、鼓噪、僵硬、刻板的人工建筑中踯躅,身体和灵魂也一道萎靡、羸弱、发霉、凋零;久久的蜗居,易使我们视野狭小、胸怀逼仄、肌力减弱、肺廓扁平。我们需要在烦琐的生活之外,找寻一个博大的存在来承载我们的身体和心灵,让我们的世界变得更加广袤,让我们知道还有那么多奇花异草、珍禽猛兽在一已的生活之外,绵延不绝地繁衍着,让我们从此不惧生死,胸怀豁达,让我们爱好和平,痛恨战争,与万物和谐相处,与宇宙相迎。
母亲——努力生活的支柱
支撑起他活下去的,是爱的信仰。在那些空落的白天后的黑夜,在那不眠的黑夜后的白天,母亲是怎样担忧着他却又不敢触碰他那受伤却又孤傲的心。史老先生在母亲逝去后,曾这样说:“在她猝然去世之后,我才有余暇设想,当我不在家里的那些漫长时间,她是怎样心神不定与坐卧难宁、兼着痛苦与惊恐与一个母亲最低限度的祈求。”天底下的母亲可不都是如此,儿子的不幸在母亲那儿是要加倍的。她情愿截瘫的是她自己。
那些势必与从前决裂的日子,定有支离破碎的阵痛和藕断丝连的游弋,更有母亲驻立良久的身影。多少年后,他终于明白,有过自己车辙的地方都有过母亲的脚印。在这个世上,唯一永恒的不是爱情而是亲情。无论身在何方,心里总住着一个家,唱着我们童年的歌谣,触动我们鼻头的酸楚。
命运——冲破世俗的枷锁
陪伴他度过艰难岁月的,是不公的命运。对于史老先生来说,园子已与他融为一体,十五年来,他见证了园子纷繁反复地变化,也见证了园中无数的人和事。无论是那一对黄昏出现的老夫妇,还是东南角高墙下歌唱的小伙子、素朴优雅的女工程师、还是美丽而不幸的小姑娘。这些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人生轨迹。是啊,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是永恒的存在,就命运而言,休论公道。
人类的全部剧目需要苦难,存在本身也需要苦难,由谁去充任那苦难的角色则全在于命运,拯救苦难的灵魂则在于悟性。于是,不公的命运摆在面前,我们悟道:愚民举出了智者,懦夫衬照了英雄,众生度化了佛祖。
最终,史铁生懂得了:活着不是为了写作,而写作是为了活着。实如余华所言:“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人的一生可以说,每一步,每一步,都是走在回去的路上。当牵牛花初开的时节,葬礼的号角就已吹响。
或许,生命真的是别无选择的偶然存在,人生是无数生命的循环往复,克服孤独与荒谬的唯一出路就是汇入人类精神的伟大旅途。比起身体的残疾,精神的残疾更加可怕,唯有对生命价值与生存意义的不断追问,才能建立起最真诚的信仰。史铁生做到了,交织着怀疑与信仰,从个体心灵的救赎通往人类精神的灿烂星空。纵使激情常被肉体的麻木疼痛和精神的忧郁掩埋,他的灵魂却升入一片澄明。正如张海迪在《心灵的篝火》中所说,物质是坚实的,如同大地,而精神则如同天空或宇宙,有限与无限都在其中,无穷无尽地开拓成为人类永生永世的寄托。西西弗斯整日推着一块大石头上山的神话,其实也可以看作是一个哲学寓言,隐含着时间与空间的规则——周而复始,永无止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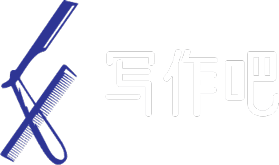
暂无评论
发表评论 我再想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