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下一张永久车票,登上一列永无终点的火车。”我想每个人都是这样的吧,这样孤独,而这种孤独是永远无法消除的,就如水一般,悠长不断,你越用手碰它,它就会越伴随着你。就如李煜对于寂寞与愁的感慨一般“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
而这本百年孤独中描写的是十九世纪中期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一个多世纪,几乎都处在军人独裁政权的统治下的拉丁美洲,那时的孤独是残忍的,悲痛的。那时的拉丁美洲一直在徘徊,从未前进过,就好像清朝时闭关锁国的中国,孤独得好像世界只剩下自己,自己就是一个世界。而霍塞·阿卡迪奥·布恩迪亚家族的兴衰正是他们自身的孤独造成的。
“世界上正在发生不可思议的事情,咱们旁边,就在河流对岸,已有许多各式各样神奇的机器,可咱们仍在这儿像蠢驴一样过日子。”马贡多文明的创始人霍塞·阿卡迪奥·布恩迪与妻子乌苏拉却有着非凡的胆识和开放的精神。同时,他意识到马贡多陷落在宽广的沼泽地中,与世隔绝,这样是无法让他人了解的独一无二的马贡多文明的。他决心要开辟出一条道路,让马贡多贯通外界。可惜的是,他却被家人绑在一棵大树上,几十年后才在那棵树上死去。霍塞·阿卡迪奥·布恩迪死了,连同他未开辟出的马贡多的文明,一颗还未升起就已糜落的星星。而之后的几代人,缺少像他一样的胆识与勇气的人,他们之间几乎没有感情沟通,都陷入了个人的孤独与苦闷,他们有着生理上的欲望,对权利的渴望,对求知的渴望,对暴力的崇尚,他们同时又拒绝着身边每一朵晶莹美丽的花朵,拒绝远方传来的呼唤,拒绝遥远世界投射出的光芒。和月亮与六便士中的思特里克兰德走出小镇的孤独不同,思特里克兰德的孤独是极少人能了解他画中的意思的一种找不到知己的落寞,他们的孤独是自闭,他们一个人猜忌,从未放过自己;一个人做事,从未与人交流;一个人发呆,从未想过创新。他们想要冲破孤独,却无能为力。他们的孤独,是不理解,不了解,不团结。
有句话是说情到浓时浅亦深,情意最浓的时候,一个浅浅的印记,便可刻苦铭心。那么我想对于他们来说,孤即无穷荆便弃,孤独到无人时,一簇荆棘,便让他们丢盔弃甲。钟摆能让任何东西飞起来,却无法使自己腾空。他们,每个人或许都有自己擅长的,但是,他们各自朝着自己一律的方向走去,也不会同他人的道路同到一起,将马贡多的文明腾到世界,让世界看看。
想必布恩迪亚家族的第七代继承人,张出了一条猪尾巴他刚出生就被一群蚂蚁吃掉就是对他们这种不创新,不走出自身建造起的小黑屋行为的讽刺与惩罚。倘若将猪尾巴代指他们的不团结,那么,蚂蚁就是那种能让他们走出黑屋的曙光,一把利刃无比的刀。
山本耀司说过,“自己”这个东西是看不见的,撞上一些别的什么,反弹回来,才会了解“自己”。所以,跟很强的东西、可怕的东西、水准很高的东西相碰撞,然后才知道“自己”是什么,这才是自我。
当闭关锁国的清朝遭受到了外界剧烈的撞击,八国联军强烈的侵犯,清朝这才打碎了自身为自身建造的“大清王朝富可敌世”的臆象,从“茧蛹”中走出,才意识到外界的经济已有经济革命,中国并不强,中国还有一大段路要赶。同样,这个家族的灭亡也应当让更多人,让世界知道,既然孤独不可避免,那么我们就要理解这种孤独,无从止歇地从满地荆棘中创造出属于自己的路。
加西亚·马尔克斯曾说:“拉丁美洲的历史也是一切巨大然而徒劳的奋斗的总结,是一幕幕事先注定要被人遗忘的戏剧的总和”,文中的家族由于蕾蓓卡的到来,纷纷患上了失眠症。犹记得,蕾蓓卡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只能咬着自己的手指,她多么孤独呀,挂上黑幕的天空下仅剩她一人醒着,熬着漫漫长夜。这也是在启示我们,被遗忘的历史,它,也很孤独啊,我们不应该忘记它,抛弃它,而是,将它从孤独的泥沼拉出,携它一起,奔向未来。
生未百年,死不孤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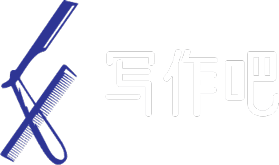
暂无评论
发表评论 我再想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