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兰河传》是民国女作家萧红所著。它正如著名作家茅盾所说:“一首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萧红以自己小时候的经历和口气,写成了这篇“如诗,如画,如歌”的小说。
全书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第五章,讲胡家的团圆媳妇。团圆媳妇是个童养媳,才十二岁。她的婆婆很会持家,对家里的家禽家畜很是爱惜,对鸡鸭猪狗都舍不得打,怕打了猪不长肉,怕打了鸡不生蛋......唯独对小团圆媳妇,却毫不留情,每天打八场骂三场,还美其名曰:不打成不了好人。结果,打出病来,也不去大夫那儿治病,迷信地东家要个偏方,西家讨个秘方,把团圆媳妇放热水里热昏,再用冷水浇醒。如此这般折腾了许多次,活生生地把这个十二岁的小姑娘折磨致死,人财两空。
从这个故事里,我不仅读到了一个生活在公婆打骂下的童养媳悲惨的命运,更认识到那个时代女子低下的地位。书里说到,当地男人打妻子的时候,都会理直气壮地说道:“娘娘(庙会上的子孙娘娘)还得害怕老爷(子孙娘娘的丈夫)打呢,何况你一个长舌妇!”可见,男人打妻子,婆婆打媳妇在那个年代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连明媒正娶的女子都难逃脱被打骂的命运,更何况一个地位卑微,甚至可以说半是媳妇,半是佣人的童养媳。
其实,即使小团圆媳妇没有被折磨死,她也会和那个年代大部分女子一样,默默地为别人走完一生,不知道自己的生命何去何从。被三从四德绑架了人生观的女孩子,一生只知道完成三件事:出嫁,生子,持家。她们的一生,仅仅是服从,仅仅是一个附属品:从父,从夫,从子。即使是大户人家的女儿,也往往没有属于自己的完整的名字。她们的姓就是她们的标识。父姓上冠以夫姓,便伴随她们的一生,直至刻在墓碑上,留下一点她们曾经来过的痕迹。 从“xx氏”,我们无从得知她是谁,有着怎样的音容笑貌,只能看到两个家族的联姻。她们代表的不是自己,只是一个代号,一个附属品,一个婚姻证明。在时代的限制下,她们只知道自己是某某的女儿,是某某的妻子,是某某的母亲。她们并不知道她们还有一个身份,那就是“我”—— 作为一个“人”的真正自我。 正因为没有自我意识,她们不知道自身的尊严,当然也无法认识自身的价值,只能在打骂歧视下,或痛苦或麻木地走到人生尽头。书中还提到,有些媳妇不堪忍受婆家的暴力或冷遇,回娘家诉苦,可是母亲却告诉她这是“命”。 这些年纪轻轻的女孩子,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悲哀甚至痛苦的“命”。有些人实在不堪忍受,只能轻生以求解脱。所以,生在那个时代的小团圆媳妇,她的命运注定是一场悲剧。
我特别关注这个章节,还有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到今年年底,我也是十二岁。 幸运的是,我生在一个民主而开明的时代: 男女社会地位平等,每个人都可以有属于自己的名字,拥有自由的意志,怀有独特的梦想,所以我拥有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生。 我认为这样才是正确的。人生而平等。既不应该有地位,职业的歧视,也不应该有性别的歧视。在我们周围,优秀的男同学和女同学各领风骚;我们放眼社会,各行各业的男女精英各有千秋。性别,本不存在“谁比谁优秀”或“谁比谁差”的问题。无论男女,作为“人”,不仅有社会责任,家庭责任,更需要为自己负责。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个人都有无穷的潜力,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长,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梦想。 同样十二岁的我,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在大千世界里行万里路,在梦想成为一名化学家,在梦想着诺贝尔的荣耀。我深深地同情同龄的小团圆媳妇,为她叹息,为她流泪,也为自己庆幸命运的恩宠。
千年前,《木兰辞》 用委婉诙谐的方式向男性世界宣告:“两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千年后,我们迎来了男女平等的环境。既然有幸降生在这个时代,作为一名女生,我会更加自信自强,展现自己的风采,发掘自己的潜能,追逐自己的梦想,努力活出自主的人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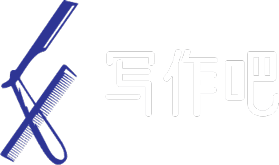
暂无评论
发表评论 我再想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