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难风雨故人来
他早已准备好了答案。在那逝去的分分秒秒内,反复吟诵的四十四年前的答案。
—题记
马尔克斯是个神奇的老头儿。曾经他信手胡写的《百年孤独》掀起大文艺阅读的狂潮。人们或站或坐,或俯或仰,苦苦研究那祖祖辈辈都叫一个名字的怪异家族。于是这不甘寂寞的老头儿看世人贪婪的模样觉得还不过瘾,便又涂鸦了一部作品,一部被他自己称作“最好的作品、发自内心的创作”:《霍乱时期的爱情》。
这名字甚是诡秘。霍乱之下的爱情,光是想想便有血色的惨烈,不只是生离死别,还有拼尽全力的力挽狂澜,是明知渺小也要与命运对峙。越是猜测不透越是神秘。我反复揣摩着这个奇异的名字,心头千回百转。
于是在一个晨光熹微的清冷的早晨,我翻开了这本书。作者以一个老人的身份,讲述了年轻时一段执着疯狂、如今看来却平淡无奈的岁月。男主人公阿里萨在六十岁的时候迎娶了自己十六岁时候的情人费尔明娜。两个人共同把满屋子的回忆付之一炬,然后登上一艘没有终点的霍乱之船。他牵着他半个世纪以来最深情的幻想——哪怕她已经没有了年轻光洁的容颜,没有高傲轻盈的步伐,没有亮晶晶的美丽的发饰——她现在同他一样是个可怜的老人,她身体的每一个角落都肆虐着张牙舞爪的死亡的气息,她口腔里有着老人特有的酸臭味。但这没有影响他的爱情。可或许没有爱情。他只不过是在树起一个自以为是的盾牌来对抗时间无情的跨越他的尸体。他总是活在一个艰难而冗长的幻想里面,在这幻想的平静中假装听不见死亡越加响亮的足音。等待到世界尽头的时候,所有人一起被救赎。
可令我疑惑的是,全文中并未提及霍乱的恐怖。甚至全文中只有几处寥寥的带过了病死的人们,却丝毫没有波及主人公所在的世界。他们像是活在世外桃源。心下犹疑,于是再读书本,恍然大悟。因为费尔明娜、阿里萨和胡尔比诺医生,都不应该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他们本来就不真实。因为爱恨生死对于他们来说,只是跨越无知走向成熟的工具。他们当然不是凡人,理应该无法感受人间的折磨。作者虚拟出一个空间供他们游玩一辈子,已是最大的恩赐。
这么想着,我心下惆怅。原来那份跨越整个青春的爱情,也是虚幻。杜拉斯曾经奢求一份不会衰老的爱情,期望着有一天每一个男人向她走来对他说:我认识你,我永远记得你。那时候你是年轻女人,人人都说你美。今天我来就是想要告诉你,你比年轻时更美。那时你是年轻女人,但我更爱你现在饱受摧残的容颜。叶芝曾经喃喃的念着:多少人爱慕你年轻欢畅的时辰,爱慕你的美丽,真心或是假意。而我却爱你那朝圣者的灵魂,爱你苍老的脸上,痛苦的皱纹。在衰老的逼迫之下,人要如何感知生命的存在?罗彻斯特在对简的告白中说:我一压那娇嫩的肩膀,就感觉某种汩汩的活力流入我的身体。——是的,人们靠爱来感知。泰戈尔说,不是因为我活着我才去爱,我要爱,顺便活着。
我的外公外婆,是温吞慈祥的一对老人。日日白头灯下,两个人把一种叫做婚姻的生活,过的四平八稳。只是有一次,外公出门有事,把东西落在家里。趁着还没走远,外婆站在窗口伸长了脖子,眯这眼望着他的背影,不知为何却红了脸,欲言又止吞吞咽咽。最后她还是对我说:快叫住你外公!我冲窗口随便一喊,外公便止住脚步。这事儿过去了之后,我总是奇怪外婆那一瞬间的反应。直到我看到一篇文章叫做《无法叫出口的名字》我才明白,越是珍惜,越是熟稔,越是在午夜梦回中千百次的嗫嚅,越是不敢在众人面前大生呼喊。即便多宠爱我和妹妹,多担忧妈妈和舅舅,外婆心里最柔软最敏感的部分,还是无所撼摇的为外公保留了下来。
所以无论天长地久,路遥马亡;无论青梅枯萎,竹马老去;无论六十岁的费尔明娜是否还拥有十六岁的剔透明艳的容颜,她都将走进一个沉淀了半个世纪的人的怀抱中。夜夜依偎彼此衰老的躯壳,忍受命运讥诮的玩笑。所以在全文的最后,当费尔明娜问阿里萨:那我们究竟要漂泊到什么时候?——这是她第一次以我和你的身份,说我们。——阿里萨说出了那个他早已经准备好的,反反复复萦绕在舌尖的答案。他守着这个答案像守着一座灯塔,在每一个海风遥远的夜晚由他亲手点亮的灯塔。他坚守了这么多年,快要到他老的连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坚守什么的时候了。现在他终于明白,那个答案便是为了现在这一刻准备的。准备给天下所有有情人,准备给生活本身。一个发自肺腑的答案。
——一生一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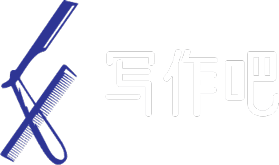
暂无评论
发表评论 我再想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