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审视,沉淀时代浮华——读《傲慢与偏见》有感
谈起简·奥斯丁的著作《傲慢与偏见》,许多人可能会想到书中无数的舞会、纸牌以及夹杂俏皮话的琐碎闲谈。正如作家伍尔夫所说:“在所有伟大作家当中,简·奥斯丁是最难在伟大的那一瞬间捉住的。”
也正因为此,后世的评论家对《傲慢与偏见》的文学价值众说纷纭。肯定评价诸如埃德蒙·威尔逊,他认为奥斯丁的作品“与莎士比亚一样经久不衰”。而夏洛蒂·勃朗特曾对其大加指责。在1848年夏洛蒂致刘易斯的信中,她质疑道:“没有诗情,能成为伟大的艺术家吗?”她认为,《傲慢与偏见》虽然将上流社会的绅士淑女刻画地惟妙惟肖,但“涉及人的心灵,还不及涉及人的眼、口、手、足的一半”,“是明智的,现实的,但不可能是伟大的”。
诚如夏洛蒂·勃朗特所言,《傲慢与偏见》的故事建立在大量豪富名流的宴饮闲谈上,以及对世态极其平静而理性的描写。但这些看似平淡的叙述背后,难道真的没有穿透心灵的力量吗?
让我们回到《傲慢与偏见》中浪博恩的那几间宅邸。以班纳特家为主线,奥斯丁描写了各有特色的爱情与婚姻:吉英与彬格莱,伊丽莎白与达西,夏绿蒂·卢卡斯与柯林斯牧师,丽迪雅和韦翰……不过,相对于那些以大量篇幅描绘热烈爱情的小说,本书所强调的是“婚姻关系”,主要是经济需要而非情感需要。故事一开头宣称:“凡是有财产的单身汉,必定需要娶位太太,这已经成了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然而,小说中却有许多情节巧妙地构成了对这一“真理”的讽刺。如书中的班纳特一家,由于班纳特先生的财产只能由男性继承,而他只有五个女儿,因此班纳特家的小姐们只能寄希望于与有财产的绅士成婚。又如地位尊贵的咖苔琳夫人执意要将女儿安娜嫁给外甥达西,以期“把两家的地产合起来”。更不用提有两万英镑嫁妆的彬格莱小姐,对年进一万英镑的达西先生穷追不舍……可以说,作者真正要阐明的“真理”是,这种婚姻需要并不来自“有财产的单身汉”,而属于依附于他们的妇女!
对这一真理的最生动注解,莫过于书中夏绿蒂·卢卡斯和柯林斯牧师的婚姻。卢卡斯小姐时年已二十七岁,相貌平平,已经成了“老处女”,家境又不富裕,想追求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只能是梦想。而与柯林斯牧师的婚姻,能够为她提供一个“可靠的储藏室”,日后不至于挨冻受饥。因此,聪明睿智的夏绿蒂只能让自己委身于一个头脑死板、虚情假意的丈夫。用书中的话说——“只要不想起柯林斯先生,便真正有了一种非常舒适的气氛。”有趣的是,在妻子舒适宽裕的婚后生活中,所谓“需要娶位太太”的富裕绅士却仿佛没有存在的必要。这不正是作者奥斯丁对开篇那句“宣称”的莫大讽刺吗?
读《傲慢与偏见》,我仿佛看见在平实而轻快的文字背后,作者简·奥斯丁正用一双宁静如湖的眸子注视这个社会的浮嚣,露出蒙娜丽莎般的微笑。她轻轻揭开社会表象华美的帷帐,露出令人震惊的事实:社会中多数婚姻的实质,无非是金钱交易和利益的结合。
由此可见,奥斯丁在《傲慢与偏见》中非但没有忽视“心灵”的存在,反而对人的心理作了生动的反映。而她并非用热烈的语言给读者以“心的悸动”,而是用利剑般的目光穿透它,跳出个人内心的情感波涛,用力透纸背的文字精准揭示了社会的普遍心理,探索了人性的深处,给人以持久的思想震撼。
《傲慢与偏见》诞生的18世纪末,拿破仑正野心勃勃想要征服欧洲,机器大工厂正隆隆作响。在那个风起云涌、浊浪排空的时代,那些冲锋陷阵,勇于呼唤女性觉醒的开拓者和旗手固不可缺,但如简·奥斯丁这样,用冷静的头脑透视社会人生,并用平和细腻的笔触将其思维成果精准呈现的沉思者,则尤为难得。
物走星移,奥斯丁和她的《傲慢与偏见》已同我们的社会隔开了两百余年的岁月。然而,她理性务实的精神和对社会现实的清醒认识永不过时,在风云变幻的21世纪,这依然是时代的刚需。新的时代不仅需要开拓创新、叱咤风云的“弄潮儿”,也应当有这样一类人:他们不求建功立业,不在时代的海涛上拾贝,却如白鸥在大海的上空盘旋,密切注视着波浪的一起一伏。他们用敏锐而理性的头脑滤净时代的喧嚣,审视繁华表象之下的问题所在,避免人类偏离正确航道。他们不是时代的创造者,却是时代的守夜人。
思绪飞扬,我仿佛又见到了宁静的英格兰乡间——这也是简·奥斯丁的家乡。田野旷远,牛羊安详,时间仿佛静止着。田埂上,有一手握纸笔、双眸如湖的女子,久久沉思,将深邃的目光投向无限远方。在她平静的凝视中,一切时代浮华都如尘埃般慢慢沉淀,留下一片高远而碧蓝的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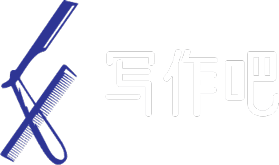
暂无评论
发表评论 我再想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