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篇】
明朝,没有元朝的铮铮铁骑,没有清朝的风雨飘摇,它静静地潜伏在历史的穴罅,呻呤着属于它的孤寂。 -----题记
(一)黄仁宇的“大历史观”
近日拜读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此书英文名为“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可直译为“平淡的1587年”。黄仁宇,只是依稀记得他的“大历史观”。由于孤陋寡闻,不能从专业的角度解释“大历史观”。 最初我觉得历史是由一个个事件组成,既然是发生过的事实,那么历史书的工作就是把这些历史事件罗列出来告诉人们过去曾经发生过些什么。人们掌握的史料越详细,就越接近历史"真相"。后来才知道书写历史时还有所谓的"历史观"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对历史持有不同观点的人眼中的史实是不同的。大概这也就是方法论上的差别。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中很明白地指出他所持的是大历史观。所谓的大历史观就是注重历史事件背后的大的政治、经济、社会背景,而不纠缠于具体的人人事事,因为所有人物的"贤愚得失不足以更改上述历史发展的程序"。
以前,屡次在书摊上和那本书擦肩而过,直觉固执地认为《万历十五年》如传统史记般琐碎地描写该年事记。其实该书是以1587年为支点,将明后期的历史支撑开来,更大的意图在于从人性角度阐释中国文明史。
书,特别是一本沉淀了历史精髓的书,是需要一颗宁静的心去解读。拿到书的时候,装帧显得很朴素。相对其他小说类读物,淡淡的封面不禁渗透出深邃的历史。于是就一天看一点,渐觉历史大潮从心中涌过。从首辅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模范官员海瑞、将军戚继光、哲学家李贽到活祖宗万历皇帝,无不叙述了他们在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中饱受煎熬,无论是皇帝还是官员,这些人最终都没有功德圆满,甚至身败名裂。张居正最终被查没,万历自己死后也无法同最爱的郑氏同陵,海瑞则在大家的摒弃中挣扎......“一个大失败的总记录,”引自书中的话。
(二)首辅之殇
张居正几乎开创了“万历盛世”,把明朝推向辉煌的历史顶峰。以前只知道张居正生前身后的强烈反差,兀自归咎于万历的“逆反报复心理”。读后感触颇深,幡然醒悟其真正原因乃是他的强势行政模式和作风同当时的“文官政治体制”格格不入。他在世的时候没有发挥他旷世的精明干练发现“一项政策能否付诸实施,实施后或成或败,全靠看它与所有的文官的共同习惯是否相安无忧,否则理论上的完美,仍不过是空中楼阁”,他忽视了他所要改变的东西正好是当时落后的生产方式与政治现实相平衡的产物,他忽视了中国两千年来封建体制的症结就在于道德代替了法制。于是他的失败和海瑞被视为异端就理所当然的。张居正十年鼎力革新,也受尽怨谤,最终人亡政息,至他身后,与他交好的还屡受其株连,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政治家最大的失败。而在其后的申时行,也许就领会到了这一点,他开始同文官体制妥协,甚至宁可被看作是大和事老,被批评为牺牲原则的政客,但依旧坚持折中调剂的原则。一切的一切,目的也是为了让国家机器的稳定运转。
于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首辅,变成文官体制与封建皇权的缓冲剂。一旦缓冲失效,夹于中间的首辅就不得不“引咎辞职”,成为冲突的替罪羊。首辅犹如深陷历史漩涡的一叶扁舟,注定沉沦。
所以说,从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政治家为保障社会的稳定,而有可能采用保护落后来作为手段之一,在某种程度来说,也是一种政治家的睿智,因为当时落后的一方占据主动权。因为这样,无论从国家资源还是个人资源以及发展中可能付出的社会成本都有可能是最小的。
在上层文官集团和下层成千上万的农民之间,在多达两万人的文官集团内部,明朝如此庞大的国家所赖以维持秩序的是儒家的“孔孟之道”。换句话说,这样一个泱泱大国并不是靠现代化的法律和理性的制度而是依靠道德来维持的。但是,道德不过是一些抽象的准则,真正在人与人之间起作用的是"礼",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礼保证了整个社会运行秩序。
无奈的是,这腐朽的制度就这样肆无忌惮地不断创造一幕幕历史的悲剧。
(三)怠政的背后——万历从阳到阴
自汉代儒家思想上升成为意识形态之后,历来统治者的目标都是一致的:用道德来保障乡土社会基本秩序,而不去顾及经济技术上的进步。事实上,道德以及它的外在准则"礼"务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力图摒弃一切竞争因素,鄙视任何经济和技术上的努力,其结果是几千年来乡土社会几乎是静止的,历代皇朝更替不过是历史的简单循环。黄仁宇指出在这样的社会中,法律极端落后,但并不表明国家的运行是无序的,相反,它依照道德和"礼"的秩序运行。明朝到万历年代所面临的问题在于表面上倡导的道德与人们实际上的行为已经严重脱节,这个矛盾已经严重到人们对道德和"礼"丧失信心并且无法维持下去。比如万历皇帝看透了道德与行为不符合的阴阳之别,拒绝用"礼"来表率天下,使得朝野上下对道德进一步失去信心,更加肆无忌惮地发挥"阴"的一面。
作为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万历皇帝曾几何时也想励精图治,甚至愿意努力去实践"礼"来建立人们对道德的信心,当他看穿了所有人的阴阳两面之后首先对道德丧失了信心。他的消极怠工并不是针对某个官员而是对这整套道德礼治体系。明朝后期道德和"礼"的确发展到畸形。这一整套道德和礼治体系一旦被建立起来就不再受人们所控制而是处处限制人们的行为。一直以为传统社会的皇帝可以为所欲为,呼风唤雨。看过《万历十五年》才根本改变了我的看法,皇帝不过是整套制度系统当中的一个角色,而且最受整套系统的压抑和控制。
有些史学家,粗鄙地认为万历皇帝是慵懒的。其实,他是睿智的,看透了体制的本质。他是优柔的,放弃了对体制束缚的抗争。
(四)饕餮悲剧
至于其他人如抗倭名将戚继光、清官海瑞等等没有一个不是这样一套制度下的悲情人物。
在《万历十五年》中,我们可以看到由于私人道德和公共道德相混淆,对人的一切评价最终归结到道德问题,人们就不得不生活在虚伪的面具下,所有人都隐瞒私欲表现出道德崇高的样子,加深了每个人阴阳两面的分化。阴阳两面的严重分化的结果就是表面上一套实际上一套,令所有人都不再相信道德。黄仁宇指出,儒家思想的道德力量在人们对它相信的时候是具有非常强大的作用的,像文天祥这样文弱书生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例子是举不胜举的。而当所有的文官集团和所有的民众都不再相信道德时,这样的统治就岌岌可危了。所以问题的根本不在于以德治国有问题,而在于私人道德渗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压抑了人性和自由,但压制不了的私欲以"阴"的一面存在和膨胀。
事实上,道德都成为了最美妙的工具,自大汉王朝开始,就以道德为根基建构社会制度,但德治始终是遥不可及的梦想,当管理体系中的大多数成员都把道德当成有效手段,整个社会呈两幅画面,一方面,道德追求是人人挂在口头的目标,然而私下大家都非常默契对追求自己的私欲。出了清官就是楷模——楷模本身就意味着稀有罕见,然后大家都怀着万分景仰的心态仰望海瑞,心中却想着自己的勾当,却谁也不肯去做海瑞,这就是中国政界的现状。这也是中国整个社会状况的缩影,绝大多数人都将仁义道德披上,穿上这件漂亮绚烂的衣服,以高尚的名义,行苟且之事。
(五)史海回眸
历史就是这样神奇,总能创造出匪夷所思的故事留与后人去猜。
历史,就是这么客观地前行。放宽历史的眼界,伸展历史的触角,历史的书写应该还原历史发展真实的轨迹。历史的真相往往隐藏在细节中,需要我们去体会和研习,而不需要他人直接的结论。
感谢黄仁宇先生,献给我们这么好的一本书,更感谢他独特的历史视觉。不同的人看《万历十五年》能看出不同的东西,甚至有人从中悟出了许多管理学方面的心得,我更关心的是黄仁宇在解释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时对当时的中国社会结构的深层次分析。
从《万历十五年》读出的不仅仅是明朝万历年间的中国社会更是当前中国社会的影子,我们需要做更多这样的工作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社会面临的种种特殊的问题。
【第2篇】
说句实话,很多人向我推荐这本“好书”,可我读起来味同嚼蜡,总算硬着头皮读完了,却不以为然。
我很敬佩黄仁宇的敬业精神,按照他讲的,教书之余,每日“走马观花”浏览了一遍133册的《明实录》,竟然用了2年半的时间。凭这份毅力,足使大陆的学者们惭愧了。只不过,掌握丰富的素材,未必有令人信服的成果。
读了整本书,我的唯一感受:全中国就那2万多官员和皇帝是活物,他们按照先哲的指示,决定着国家乃至民族的未来,其他的行尸走肉已经完全丧失了自主意识和现实影响力了——这绝不是象我这样一个接受马列毛史观的人说能接受的。
以前也读过一些西方人写的传记、史书,很明显黄的书是和他们一脉相承的。不论对一个人,还是一个国家,他们对自己所熟识的局部的兴趣远大于整体的兴趣;同时他们早早设好了一个完备的理论框架,框架里的各类概念、公理、定理都已按照他们自己的逻辑完成推定;对于“史实”及其驱动力,沿着这一套理论框架展开自证,并将主观的判断以貌似平和又毋庸置疑的口吻陈述。因此读他们的书,往往被他们牵着走进他们的思想迷宫,你要么全盘接受他们的思路,这样才能走出来;要么陷入这个迷宫,既不能接受作者,那么自己也将迷失——因为整本书的素材,其实都是作者根据自己的需要来甄选的。
当然,这一套方法并没有错,黄仁宇是很仁慈的。哪个专家,哪个政党,哪个政府,不是拿这套方法来让老百姓钻进自己的迷宫呢?走进去吧。按我指引给你的道路走,前面有温饱,有小康,有高级阶段,不要往旁边看,贪污腐败只是个别现象,卖淫嫖娼更是国际惯例。不想走,可以!你会下岗,会买不起房,会男盗女娼为社会所不容,都因为你没有按照我指引的道路走。入口有拿枪的警卫,你退出迷宫已没有机会。
可见一个成熟的历史观和方法论,还有一群与你同呼吸共命运的人,是读懂书的关键。
重回正题。读《万历十五年》,倒让我思考了中国儒家、法家、道家、佛家对中国人及中国社会的影响。
分析这四家的特点,很有意思。
儒家、法家是提倡入世的,道家、佛家是提倡出世的。
儒家求仁,并逐渐演化出性本善的出发点。法家的理论出发点则是“本恶”。因此儒家讲究自律自省,讲道德教化,用前两年党中央的口号:以德治国,更具体化为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
法家则承认人类的阴暗面,而人类的阴暗面一旦温度、湿度合适,就会发芽,会一发而不可收拾。因此法家讲纪律,讲制约。
道家很有意思,他是修今生的,修长生不老,他只在乎自身,几乎不讲组织,不思考全人类。这也是为啥中国的道家,始终没有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道教”。
佛家不修今生修来生,今生就是受苦赎罪的。但大乘佛法讲普渡众生,他思考人类,也努力“拯救人类”。(能不能拯救另说。如果说拯救就拯救,我们现在不是在极乐世界,就是在共产主义了)因此佛家成为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宗教,尽管在其发源地已经式微,但在中日和东南亚的影响力极大。
从个人修为的角度考虑:
法家几乎是不必考虑的。他既然承认人的罪恶,并寄希望于律法,自身修为自然是多此一举了。
儒家讲究自修,所谓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修身。这属于理论和方法都具备了。
道家不讲道德,讲的是天人合一,这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和方法,因此他往往成为儒生被现实所迫后的无奈选择。
佛家讲四谛,将业力,上辈子的事情,你既然无法改变,便只有接受,并诚心改过。
从国家治理的角度考虑:
法家讲律法,这是精髓。但是,绝不可以公开提倡法的精神。既然人人有恶,是天性或是现实造成的,那么造反就有理!
儒家讲修身然后齐家而治国平天下,而且要效法先圣。这是很高尚但又很幼稚的想法,看看美帝、法帝以及野蛮民族的所作所为,就知道有的人是很无耻的。一个人可能可以自律,可能可以管住自己的家人,但他仅仅靠道德就能教化千里之外的人?这是被蛇咬死的农夫的愚蠢。
道家在这方面也是缺失的。看看老百姓心中的天庭,玉皇大帝连自己的女儿的管不好,就别说管天国了。
佛家也很有趣。他不讲究治国,他讲究的是终生平等,这点必然是为统治阶级不能接受的。但是他的前提很好,即你这辈子的苦,是你上辈子作的孽。因此佛家京城成为麻痹人民的思想基础。
回过头来,我们就发现,中国几百年来,修身的根本是什么?治国的根本是什么?
修身的目的不同,有人出世,有人入世。但可以肯定的是,出世的人,必是儒或法。但凡信道、信佛的出世人,不是假的。只有心灰意冷的入世人,没有风月场上的出世人。
治国就有意思了。没有任何一家的理论是适合治理一个国家的,只有阳奉阴违了,外儒内法,外佛内法都是不错的选择,但外儒内法无疑更完善。过于强调儒法治国,必然柔弱以亡,宋、明都亡于此;过于强调以法治国,必然道德沦丧,亢奋而亡——我们已经看到了英帝的衰败,也将很快看到美帝因此而败。
这也是中国为什么在过去2000年整体上领先于世界的原因。只可惜,宋明两朝,都有所偏颇,倾向于儒生治国,特点就是法古德治,因此被蛇咬是必然的事情。元、清两朝就不说了,野蛮民族统治文明之邦,本身就是个悲剧,是对人类历史的羞辱。
【第3篇】
万历十五年,就是公元1587年。 黄仁宇先生为什么要写这一年呢?当然书中所写的事件,也不都是在万历十五年发生的,上下好几十年的事情都有,有的还是几百年前的事情。而万历十五年,也就是公元1587年,其实平平淡淡波澜不惊无关紧要的一年。书中的开头一段就是这么写的:“公元1587年,在中国为明万历十五年,论干支则为丁亥,属猪。当日四海升平,全年并无大事可叙,纵是气候有点反常,夏季北京缺雨,五六月间时疫流行,旱情延及山东,南直隶却又因降雨过多而患水,入秋之后山西又有地震,但这种小灾小患,以我国幅员之大,似乎年年在所不免。只要小事未曾酿成大灾,也就无关宏旨。总之,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
还是那个问题,既然如此平淡,为什么要用一本书来写呢?而且书名就是以那一年命名呢?这就跟黄仁宇先生看待历史的观点有关。黄仁宇先生强调“大历史观”。什么是“大历史观”?不妨引用黄仁宇先生的一篇文章《<</SPAN>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中的一段话来说明:“以短衡长,只是我们个人对历史的反应,不足为大历史。将历史的基点推后三五百年才能摄入大历史的轮廓。《万历十五年》已经初步采取这种做法。所以叙事不妨细致,但是结论却要看远。”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就好比是在做切片研究。通过研究切片,来认识整个生物体的构造以及存在的毛病,通过研究万历十五年这一年,来揭示历史,这一年乃是历史上失败的总记录。
那这一年有什么事情值得记录呢?这一年海瑞与世长辞。海瑞清廉,刚正不阿,执法必严,执法为民。举例:海瑞死的时候,吩咐随从人员,要及时归还二两银子、一只鸡;海瑞为母祝寿买了两斤肉;死的时候连棺材本都没有,好像是靠领人接济才得安葬;海瑞还驱逐总督胡宗宪之子,胡宗宪也是抗倭大将,因为胡宗宪之子鞭打驿站人员,认为他们招待不周,表明海瑞不谄媚权贵。剥皮实草的极刑,朱元璋定下的规矩。
这一年戚继光也去世了。在张居正死后,戚继光就被罢官,和为数不多的几个人物有交往,黄仁宇先生在戚继光这一章中,用了标题孤独的将领来形容戚继光。戚继光的练兵、抗倭功绩不需要我多说。戚继光的罢官跟明朝的官吏制度也有很大的关系。武官不如文官,武官总比文官低。武官调动频繁,防止上演唐朝的藩镇割据现象。武官中的总兵最多只能管一省兵力,不可跨省。戚继光任蓟州总兵,防区为北京东北一带,拱卫京畿。有张居正的扶持才能在蓟州总兵任上达十五年,等于他前任十人任期的总和,张居正一死,他就被调任广东总兵,虽然是平级调任,但已经失去了拱卫帝都的重要地位。再过一年,清算张居正的运动达到高潮,戚继光革职。可以说文官的派系斗争牵连到武官。
那是不是文官之间的派系斗争导致了明朝的衰弱直至灭亡呢?恐怕还不能那么简单的去看。张居正改革,“考成法”,用现在话来说就是政府绩效考核方式;军事方面,为了防御蒙古鞑靼入寇边关,张居正派戚继光守蓟门,李成梁镇辽东,又在东起山海关,西至居庸关的长城上加修了“敌台”3000余座。他还与鞑靼俺达汗之间进行茶马互市贸易,采取和平政策。从此,北方的边防更加巩固,在二三十年中,明朝和鞑靼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争,使北方暂免于战争破坏,农业生产有所发展;经济方面,整顿赋役制度、扭转财政危机,这是张居正改革的重点。他认为赋税的不均和欠额是土地隐没不实的结果,所以要解决财政困难的问题,首要前提就是勘核各类土地,遂于万历八年十一月,下令清查全国土地。在清查土地的基础上,张居正推行了“一条鞭法”,就是讲田赋徭役统一折算为银两,改善了国家的财政状况,还以福建为试点地方,想从此推广。还有其他方面的改革治理,比如治理黄河,改革军费的供给体制。张居正的这一系列改革,都几乎随着他的死而消失,连跟他治理黄河的一个官员同样受到牵连。
请容许我在说一说当时的文官制度。明朝这一朝治贪腐是很严的,用什么招数来治呢?严刑峻法。严刑峻法是事后的治理手段,平常有何手段呢?其实也称不上手段,就是官员的薪水制度。明朝的官员俸禄是很低的,如各部尚书的官阶为正二品,全年的俸银只有152两。低俸禄是为了让官员保持清贫的生活,平时居家生活不奢侈,又怎么能贪污呢?可现实并非如此,中央官员,或者说京官,他们的收入主要依靠地方官的馈赠,各省的总督巡抚所送的礼金和礼品,往往一次即可相当于十倍的年俸,尤其是到了绩效考核的时候,决定官场前途的时候,钱财物更是不能少。当了地方官,能捞的油水就更多了。在张居正改革赋役制度以前,收税是要一级一级去收的,每一级负责收税的人有自己的份子钱,先满足了自己的那一份,以及孝敬上级的份额,再拿来为国家。这种收入能不能算不合法的收入呢?那要看从什么角度去看。站在朱元璋和海瑞的角度去看,这当然是贪官污吏,应当立即剥皮实草,诛戮九族,家产充公。可是明朝的文官体系或者文官系统是很强大的,他们足以跟皇帝抗衡,当然也不叫抗衡,应该是周璇。为了党争,会去揭人家的短,但平常,大家心照不宣,你拿你的,我收我的,当官当然是为了发一笔财,彼此的默契远大于分歧。这不仅仅是在贪污受贿上如此,在个人的道德品行上同样如此。《万历十五年》中讲到一个人物,李贽,一个大家,大哲学家。在李贽风光体面的时候,大家彼此称兄道弟的时候,李贽不仅学问大,而且品行端正。可到了彼此有冲突,彼此反目成仇的时候,就指出他以前的诸种不端行为,比如教友人孀居的女儿读书,交往过密;过去曾出入与“花街柳市之间”,和风尘中人交往,有辱圣人教诲,有辱斯文。甚至当地士绅还放火烧了李贽用来讲学的亭子。这些事情,平时都司空见惯,揭短之人平时也是这么干的。
在《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中,还提到了另外一位人物,就是首辅申时行。如果说张居正是一个理想高过现实的人,在改革上雷厉风行,撇开当时的文官集团,重用自己的亲信,那么申时行却是一个现实高过理想的人,他当官有很大的现实感。他明白人,无论是官员,还是平民,都有“阴阳”两面。阳的一面就是对道德伦理圣人教诲上级命令的遵守,阴的一面就是要为自己谋私利,以及如何首鼠两端,两面为人。所以为官为政之道,就在于调和折衷,大家拿出诚意来,彼此团结和谐又不触犯自己的私利。所以申时行大多数的时候是以和事老的面目出现。下属有派系争斗了,他要去调和;大多数的官员跟皇帝意见不一了,他要去调和。可是这么一个调和大师也实现不了调和的目的。不但调和不了,还牵连于己。张居正死后清算张居正的运动就让他只剩半条命,首辅的位置已经在摇坠,因为申时行属于张居正这一派的人物,受到张居正的赏识提携才能居高位;立儲风波则是终结了他的政治生涯。万历皇帝和群臣之间在谁立为太子的意见上不一。朱常洛为长子,但万历并不喜欢他,也不喜欢他的母亲,他的母亲原本是万历母亲慈圣太后的侍女;朱常洵出生得晚,但他的母亲是郑贵妃,万历非常喜欢郑贵妃,也非常喜欢朱常洵,之所以郑贵妃能得万历欢喜,除了容貌这一因素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郑贵妃爱读书,有才,能够跟万历两人进行思想上心灵上的交流,这在其她嫔妃以至于皇后都是望尘莫及的,也因此宫女太监们经常看到皇上和娘娘一起看日落,吟诗作对。万历信佛,万历也经常和娘娘俪影双双,在西内的寺院拜谒神佛。这样的事迹能够流传下来,就表明皇帝从自己有第一个女人开始,第一个女人就是指皇后嘛,终其一生只宠幸一位贵妃,这本身就是一个稀罕的情形,当时的人认为这样的情形发生在皇帝身上是稀缺的。万历不仅在和郑贵妃一起的时间长,而且和郑贵妃在一起,流露出更多的真性情,喜怒哀乐发自内心。立儲风波是这样的,许多大臣们坚持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坚持儒家教化;可是万历当然要立自己喜欢的儿子做太子,也就是朱常洵。那首辅申时行说得难听点叫首鼠两端,在万历面前,说万历说得对,常洵如何如何优秀,要立常洵为太子;在大臣面前,又说要尊重传统,立长子为太子,申时行把解决问题寄托在时间上面以及自己作为首辅的调和折衷能力上面。可到了后来,是两面都不是人,大臣参劾他表里不一,欺骗圣上,排挤陷害同僚,万历也难办,一直拖着不办,最后见参劾他的人越来越多,自己只好上疏辞官。一个以调和折衷之道为官的人,反而被同僚的参劾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命,这无疑是一个嘲讽。
《万历十五年》这本书里面还有很多的人物事件,上推下演,就是为了通过万历十五年这一年,这一个切片,看到中国历史的一个脉络,一个衰亡失败的总记录。为什么这一年会是衰亡失败的总记录呢?难道现实不是变动不居的吗?那是因为中国的统治阶级自古以来承袭了儒家的那一套,有自己的治国方案,有自己的一套,不去考虑社会现实以及现实中的问题,不去考虑变动不居的社会现实能否配合你那一套东西,那一套理想秩序。当然也不是完全不考虑,完全忽视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当发现问题的时候该怎么办呢?儒家伦理要求统治者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当然首先是正心诚意。期待通过这样解决现实问题。可是现实的变动不居产生的问题并没有解决。中国人出了名的不精确,一个知府不知道他管辖范围内有多少良田,每年要交多少税,发生天灾了该如何应对折算;军队里的将领也不知道手下有多少兵,更不清楚他们对战争、对当兵的看法,更别说平日里的粮草操练等等。积重难返。这样的千年不变,如果说有变的话,那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可以说每一年都是一个衰亡失败的总记录。就像在跑道上跑步,每一圈跑下来看到的风景是一样的,每一个点上,每一个转弯处看到的也是大同小异。
最后引用《万历十五年》这本书最后的段落作为总结:“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丁亥次岁,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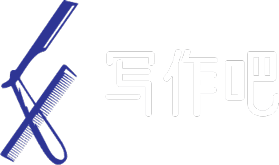
暂无评论
发表评论 我再想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