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传》由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米开朗琪罗传》和《托尔斯泰传》组成,它们均创作于二十世纪初期,无论在当时是在后世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这三部传记中,罗曼•罗兰是紧紧把握住这三位拥有各自领域的艺术家的共同之处,着力刻画了他们为追求真善美而长期忍受苦难的心路历程。书中写了三个世界上赫赫有名的人物。第一个是德国作曲家:贝多芬;另一个是意大利的天才雕刻家:米开朗基罗;最后一个是俄罗斯名作家:托尔斯泰。
罗兰认为伟大艺术家是"集体力量"的表达者,是群众、各民族和人类巨大激情的表达者,因为他觉得"集体力量"是一种自发的和完全不为理智所理解的东西天才艺术家的伟大,包括所有天才的伟大,按照罗兰的看法,绝不在于他具有某种超人的、非凡的力量。恰恰相反,一个杰出的人;尤其是一个天才,要比普通人更紧密地同现实生活结合在一起,他了解生活的本质要比别人更深刻,他预感历史大变动的临近,要比别人早一些。
早在本世纪初,罗兰已经接近于对杰出人物的作用的这样一种理解,而且这种理解在他的传记特写中得到了体现。随着他研究贝多芬和米开朗基罗生平的日益深入,尤其随着他为还没有写的其他几部传记收集的材料日益增多,他越来越清楚地感到那些伟大人物的内心世界的复杂,而他原先是打算把这些人物当作意志坚定和性格刚强的榜样来加以描写的。这就妨碍了他把拟订好的丛书计划继续下去,不过这并没有动摇他对所选择的题材进行处理的美学立场。伟大人物是有缺点的,他们在所走过的道路上也有过动摇和错误,然而他们的伟大正是在于他们有时善于--用痛苦的内心斗争作为代价--战胜弱点和克服动摇。
罗兰在《米开朗基罗传》的序言中写道:“我没有给那些高不可攀的英雄们建立纪念碑。我憎恨理想主义,因为它胆怯地回避生活上的痛苦和精神上的弱点。然而,太容易受一些花言巧语蒙骗的人民应该牢记:有关英雄主义的一切谎言是由于胆怯而产生的!英雄主义就是看到世界的本来面貌,热爱这个世界。”这一思想,在该书的结尾中又重复了一遍:“难道,我应该象其他许多那样只去描写英雄们的英雄主义,用一块盖布把他们跌入的整个痛苦深渊罩上,可是不能这样做!真实高于一切!我不能用谎言去答应给自己朋友们幸福!我不惜一切代价非这样做不可,我只能答应给他们真实,甚至用幸福作为代价答应给他们真实,给他们勇敢的真实,并用真实这把刀子去雕刻不朽的心灵。”这一肖像是本世纪初罗兰在《贝多芬传》中刻画的。而且他还修改重审自己的这一早期作品,并持批判态度。一九三六年,他在着手他的巨著的第三部《复活之歌》的创作的时候写道:“我们研究贝多芬三十年了,在这期间,我们不仅更清楚地了解了贝多芬的生平,而且了解了一个人--人们--的生平……现在,为了一块面包,我们已经不能把贝多芬这一个人看成是想象中的英雄,看成是由不锈钢铸成的具有倔强性格的英雄。他--就象所有的人,哪怕是英雄,一样经历过乏味生活,是某些身份不同的人和可以说地位不同的人之间的战场。”生活的条件,坏境的压力使人也决不可能摆脱内心斗争。“这使他的英雄主义具有更高的价值,因为众所周知,他作出了多么大的努力。”就是贝多芬也不能完全摆脱内心矛盾。尽管他的性格独立不羁,但有时也会巴结强者。虽说他是一个不谋私利的人,但在就钱的事情同出版商和戏院经理的一些洽谈中,他却表现得极其固执而又坚决。尽管他满怀共和主义激情,然而他仍为自己的贵族身份而感到十分自豪。所有这一切怎么去解释呢?罗兰自己作了回答。“让伟大艺术家力求成为代达罗斯,给自己插上翅膀,飞向……系在双脚?上的秤砣却把他留在大地上--这秤砣便是经济上的奴役,所以他一次又一次地跌入人们共同的陷讲。在那里,他为了一块面包和可恨的贫困同别人进行了顽强的斗争。”
贝多芬许多个人弱点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由这一点造成的。对他来说,有钱就意味着相对减少依赖,因此他为了一个铜板就能固执地讨价还价。对他来说,贵族身份是一种避免受别人鄙视的工具,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这样,因为那些不敬重贝多芬这个作曲家的人,却很敬重贝多芬这个贵族身份,因而当有人对他贵族身份的真实性提出异议时,他就会大发雷霆。他的革命信念帝国警察局知道得十分清楚。这使他始终担心会遭到迫害。因此,为了避免遭受迫害,他有时克制住对巴结奉承的厌恶,在自己毫无天赋的学生和庇护者鲁道夫大公面前说上许多恭维话。在叙述这一切的时候,罗兰一味反复地说:"天才的这些错误和失败不应该把我们的眼睛遮住,使我们看不到他的伟大。这仅仅是对时代作出的不可避免的让步。确实,罗兰在这里指出的有关贝多芬个性的新观点,同他《名人传》原先的构思是不矛盾的,而只是对这一构思作了更明确的修改。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了艺术家痛苦的深度,同时也看到了艺术家道德的伟大,因为艺术家善于不顾一切地保护自己内在的人的本质,从而保护了自己的创作天才,使其不受有害的影响。
我们不能不钦佩米开朗基罗:他创作了许多作品--尽管遇到了无数的障碍。在这些作品中体现了“一股象飓风一样凶猛的强大生命力”。罗兰英雄传记的感染力并不在于肯定痛苦,而是在于克服痛苦,战胜痛苦。这一胜利罗兰本人并不是轻而易举地取得的。后来他在《伴侣》集的引言中写道:"……在我的《米开朗基罗传》的序言中,我不无痛苦地对基督教的悲观主义表示了抗议,我十分清楚在自己身上和在别人身上的这种悲观主义……?因为它导致了对人类进步的否定,而反动势力却同它结成联盟。谁同反动势力作斗争,谁就应该同悲观主义作斗争;我在自己心里也在同它作斗争,所以这绝不是一件极其轻松的事!这一斗争的痕迹在《名人传》中是显而易见的。罗兰思想上的矛盾,与其说是表现在他把自己主人公遭受的痛苦放在首位,倒不如说是表现在他多处(特别在《米开朗基罗传》中)抽象地、超历史地论证了这一痛苦,并把它解释成为是人所具有的,并且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非理性热情的影响。可是在《名人传》中,现实主义地、历史主义地看待人这一点得到了更加令人信服的和更有力的肯定。在罗兰创作的传记中的每一个主人公,最终都是被作为自己民族、自己时代的产物加以描写的。他们中每一位的痛苦经历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偶然事件的影响和人类天性的内在气质造成的,而是由社会的残酷规律造成的。在这样的社会里,一个艺术家跟大多数人民一样都是处于从属地位,都是在被奴役的人之列的。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作为非正义的牺牲品,作为社会压迫的对象的这种主题,经过罗兰的许多艺术加工同样也体现在他的英雄传记中。
“我为教皇服务,不过是迫不得已的,”米开朗基罗说,“一个教皇死了,另一个教皇即位”。米开朗基罗,自由的米开朗基罗,一辈子只能一个轭换上另一个轭,重新更换主人。尤里乌斯二世,利奥十世,克雷芒七世,保罗三世,保罗四世--他们都先后支配过米开朗基罗的才华……最神圣的和最显贵的主人们用各种古怪念头作弄米开朗基罗,交给他一些不符合他心愿的工作,强迫他去画一些以前没有完成的所有大型的新作;对他进行诽谤,在他的周围搞阴谋,想方设法离间他和水平相当的画家莱奥纳多和拉斐尔的关系;用各种挑剔和威胁恐吓去折磨他,处处替他设置障碍。他不止一次地不得不承认:“他耗费了极大的精力、才华、欣悦的灵感,结果都徒劳无益!”折磨着他的精神悲剧的主要根源就在这一点上,而不是在人类自古以来的本性上!罗兰还揭示了这一悲剧的另一个方面。在有关米开朗基罗一书中,表现出了作者高度自发的历史主义。他看到了曾被文艺复兴时期载入人类史册的事物--获得解放、令人欢欣鼓舞的事物;但他也看到了文艺复兴时斯的内在矛盾。在某种程度上说,罗兰同托马斯·曼彼此呼应,罗兰再现了那个历史时斯的意大利的气氛。他着重强调了人物的善良,描写米开朗基罗的慈善活动,报道贝多芬令人感动地关心自己放荡的侄儿(孤儿)--所有这一切今天看来都是天真幼稚的和多愁善感的。可是罗兰认为仁爱是大艺术家不可缺少的品质--不仅在崇高的志向和感情方面,而且在平时的行为方面都是如此,在许多欧洲知识分子认为善于超过一般人,站在“善与恶的另一边”是艺术家的高尚美德的时代,罗兰援引了贝多芬的话:“我不知道其他更高的准绳,除了善良之外。”罗兰选择作为自己主人公的恰恰是这样一些伟大人物,即罗兰能够通过颂扬他们的强有力的、充满思想的、焦虑不安的和热情洋溢的创作去对抗他在自己周围看到的那种庸俗艺术的伟人。论贝多芬和米开朗基罗这两本书的悲剧观点的产生原因在某种程度上在于罗兰想把这些身处逆境的天才同《广场上的杂耍》中买卖兴旺的商人、洋洋得意的手艺人和欧洲资产阶级文坛和艺坛上的居心叵测、玩弄权术的人进行尽可能地鲜明的对比。在这一方面,《名人传》同《约翰·克利斯朵夫》的紧密联系就特别易于体会了。这种矛盾,尤其理解不了这些矛盾的社会基础和历史基础。
《托尔斯泰传》同样是一部态度严肃的作品。这部作品是建立在对托尔斯泰的艺术创作、他的书信和同时代人的回忆文章的详尽研究的基础上的。在这一本书里,正如在罗兰其他的传记作品里一样,倾注了巨大劳动,不仅是一个艺术家的劳动,而且是一个研究家的劳动。应该高度评价罗曼·罗兰的洞察力。在这一本篇幅不大的书中,罗兰择取了真正本质的东西,向法国读者提出了托尔斯泰创作个性中所有最重要的方面。若是指责罗兰,说他在这里非常客观地、不加指摘地描绘了托尔斯泰的宗教观点,不仅再现了他那些自我完善和"博爱"的号召,而且照搬了他对社会主义的抨击,这都是有根据的。在这一时期,罗兰对待"托尔斯泰主义者"的哲学,完全不可能持批判态度。他对托尔斯泰的优缺点作出正确的评价那是很晚以后的事,是在十月革命之后。但是,在自己的人物传记中,罗兰以一个艺术家的嗅觉明白了。并且力求指出,在托尔斯泰的思想意识中进行的内心斗争是多么尖锐,多么痛苦;他还力求(其中包括在他对《复活》的分析评论中)指出那种勿抗恶学说对有才华的作家的创作技巧是多么有害:“宗教结局从整本书中是得不出本质上的结论的。所以,我坚信,不管托尔斯泰怎样自我表白,他在内心深处仍然无法使两种对抗的因素妥协:艺术家的真理和宗教信仰者的真理。”艺术家的真理,即现实主义问题,在罗兰的分析中占据着中心位置。早在一九O一年,罗兰就把托尔斯泰的“道德完善”同“象老年人那样病态的”欧洲的虚假伪善进行了比较,并一再肯定俄国作家的作品“具有最大和最难得的优点--真实性。”托尔斯泰作品的这一性质,便是“无情的现实主义观察”,在罗兰的书中得到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在这本书中,有一些很有意思的评语,它能帮助人们去理解。对罗兰来说,为什么同十九世纪的法国小说大师相比,恰恰是托尔斯泰更能成为现实主义的导师。自然,无论是左拉、莫泊桑,还是福楼拜,他们都善于在自己的现实观察中成为无情者,这一点罗兰也是十分清楚的。但是,托尔斯泰的无情则是别一种类型。他反对社会的邪恶,同艺术家对人身上的道德、精神、创造力量的极大信任结合起来。与福楼拜不同的是,福楼拜“认为自己的力量在于不爱自己的主人公”,而托尔斯泰则“通过现实主义的力量……使自己在任何人身上都得到了体现”,正是由于他对人们的爱,“他深入到生活的各个角落”。罗兰无论如何也不愿意这样说:仿佛托尔斯泰就是从宽恕一切的立场去看待他所否定的人物的。这一点在论揭露者托尔斯泰、论托尔斯泰的《反对社会偏见的斗争》这些随笔中说得很有分量。但是。罗兰坚信,托尔斯泰--远远胜过他那些同时代的法国现实主义者--的作品里揭露和否定的感染力是同对正面人物的优秀品质的探索联系在一起的。托尔斯泰的这些探索不管多么天真纯朴,然而重要的是,他作这一个艺术家,甚至作为一个政论家,并没有局限于“纯粹的”否定。托尔斯泰的批评始终具有创造性价值。他竭力重新建造。在托尔斯泰的现实主义中,罗兰不仅高度评价了他的社会洞察力,而且还高度评价了他对待人的人道主义的感人态度,而这正是他那创新的心理描写手法的基础。在《托尔斯泰传》中,罗兰并不打算去弄清楚一些历史原因,即俄国的现实主义,特别是托尔斯泰的现实主义之所以产生巨大力量和获得世界意义的历史原因。俄国文学同人民及其解放运动的紧密联系,文艺作品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的俄国社会生活中的特殊作用--所有这一切当时罗兰还不是很清楚的。但是在他的书里出现了一些正确的推测:人民反对压迫者的怒潮日益高涨,这对托尔斯泰产生了影响,养成了他对社会的批判态度,特别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时期。……随着新世纪的开始,革命风云四起,开始出现在知识分子中间的风潮,在人民中间扩展开来,同时纷扰不安地煽惑着成千上万备受压迫的人。这支令人望而生畏的贫苦大军的先驱者,托尔斯泰从自己的雅斯纳亚·波良纳的窗口里是不可能看不到的;民众的灾难不断,他们的风潮日益高涨,在这一局面的影响下,托尔斯泰违背了自己的学说,“同样大声疾呼向刽子手们复仇”,罗兰目光敏税地指出了托尔斯泰人民性的另一个方面:一个艺术家对民间创作、丰富的民间语言和劳动农民思维方式的高度注意。“托尔斯泰这位大师不受文艺程式化的任何束缚,就该格外敏锐地去领悟人民思想和语言的整个美妙之处。他习惯生活在远离城市的地方,生活在农民中间,他掌握人民思维的特点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不仅仅托尔斯泰的语言和描写手法应归功于人民;他的许许多多的灵感也应归功于人民。”在描写托尔斯泰的许多法国文学家中间,象罗兰那样清楚地感觉到他的创作技巧的这一极其重要方面的大概一个也没有。显然,罗曼·罗兰根据自己的一些创作上的探索,估价和领会了托尔斯泰人品的真正价值。从事《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创作,在内容丰富的长篇小说的新形式方面的探索都激励着他努力去认识托尔斯泰的历史性长篇小说的写作技巧的意义。他既清楚地感觉到了《战争与和平》的艺术结构的创新,又感觉到了这一创新同俄国现实、同托尔斯泰的生活经验的联系。“智者的天性爱好吸引了他,使他从描写人物的个人命运的小说转到广大群众和千百万人的意志在起作用的小说上来。托尔斯泰曾在塞瓦斯托波尔看到了各种悲惨事件,这些事件帮助他理解俄国民族的精神和长期以来的遭遇。罗兰说,在《战争与和平》中,"我会感觉到历史那有节奏的和可怕的步伐,在你的面前会出现一个整体,那里一切东西都是相互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小说原结尾中,“产生了生命的连续性和死而复活的永恒性的印象……未来的英雄,发生在他们之间的各种冲突都被预料到了,离开人世者的音容笑貌活在其接班人的心中”。托尔斯泰史诗性小说的这些与众不同的特点,早在大学生年代就吸引了罗兰,激励他如果不去模仿,那就去竞赛……《托尔斯泰传》同罗曼·罗兰的创作探索同样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在《托尔斯泰传》中,罗兰阐明了俄国伟大艺术家的美学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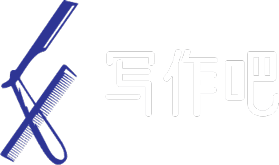
暂无评论
发表评论 我再想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