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锦年感觉她现在的头,就像有斧子在劈似的,一下一下,真是疼得要死。不过,只是要死,而不是真的死了,这就已经很好了。
就在几分钟前,她已经确认了再确认,自己现在是活着。
周围的场景,是这样的熟悉,熟悉到她闭着眼睛都摸索出来。她,是在自己的甲壳虫爱车里。几分钟前,她就是蜷在驾驶座上,趴伏在方向盘上,压到了喇叭,把自己给吵醒了。车子外头,灯光冷清,也是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了,隆裕广场B2层停车场。
刚刚她的动静大概不算小,车喇叭大概响了很久,停车场的安保人员已经找过来了,一看是这辆熟悉的甲壳虫,原本的不耐烦已经变成了小心翼翼的关心,却又不敢贸然打扰,只是不远也不近的站在驾驶座这一边的车门边。
锦年顺势看了这人一眼,眼神忽然穿过保安头顶上方,落在了这人身后不远处悬挂在高处的电子计时器。那上头显示的年份,让贺锦年的心猛地揪了起来,心脏的跳动像是格外有力,有力地要从胸腔里跳出来一样!
按下车窗,“计时器没坏吧?”
保安虽然有些莫名其妙,但还是顺着贺锦年的眼神回头望了望,“没坏啊!”
太好了,真是太好了!父亲,她这就要去见父亲。
就在一天之前,她才接到哥哥的电话,电话中的声音是那么疲惫,“贺锦年,你还要颓废到什么时候?立刻给我滚回来!爸爸,爸爸进了急救室,医生说,可能醒不过来了……”
怎么挂的电话,怎么上的飞机,她都是混混噩噩的,心里只有痛只有悔。飞机上,灯光昏暗,机身震荡,人声嘈杂,尖叫哭泣谩骂,她都没有入耳,只是心中嘶喊着,她要去见父亲!
而现在,眼睛开阖之间,她竟然回到了五年前!
顾不得别的,贺锦年立刻发动引擎,倒车,换挡,一打方向盘,一点也没有五年不开车的生疏,甲壳虫就这样风驰电掣的开了出去。
父亲,父亲这会儿应该在哪儿?按着他的习惯,因该在和平饭店他的办公室吧?贺锦年知道,稳妥的办法,就是先打个电话去确认一下。可是,她,不敢,不敢听见电话那一头,不是那个听了二十多年的声音。她要自己去看!
贺锦年的头真是疼得厉害,可就是这样,反而让她很高兴,不是说做梦感觉不到疼的吗?
隆裕广场与和平饭店都是在一条马路上,可是一个在马路的西头,另一个又在马路的顶顶东边,贴着外滩,而这条马路,又是这个城市最繁华的马路之一。但就是这样,贺锦年还是把甲壳虫开出了赛车的架势,最后看到和平饭店那个熟悉的老式转门,更是一不小心,车轮擦到了路边马路牙子。
贺锦年实在等不及泊车,一开门,抓过手提包,碰上车门,就狂奔起来。此状若疯狂,哪里还有一点点当年贺四小姐出了名的淑女样子?
进了电梯间,纤长的手指头拼命的按动着楼层钮,以前让锦年赞叹的老式电梯,这会儿真是让贺锦年急得心火烧。终于到了楼层,等不及电梯门完全打开,就侧身出去,穿过回廊,不管秘书迎上来说话,猛地推开了父亲办公室的门。
抬眼处,父亲就端坐在老式办公桌后头,鼻梁上架着老光镜,这会儿正从眼镜上方看过来。
贺锦年浑身一下子没了力气,人像是被抽了骨头一样,斜斜的倚在了门上。贺毅庚本来想训斥女儿几句的,可忽然惊讶的瞪大了眼睛,抬手取下老光镜,人已经站起来从办公桌里侧绕了过来,“锦年,怎么啦?你怎么哭啦?”说话间人已经到了贺锦年身前。
贺锦年再也不顾别的了,扑进了父亲的怀里,痛哭了起来。贺毅庚虽然心急着女儿,但也没有继续再问,而是就着这姿势一转身,把女儿带进门里,一手关上门,然后一下一下的撸着锦年的背脊,由着女儿在自己怀里痛哭发泄。
等贺锦年哭声渐渐变小,才继续刚刚的问题。
贺锦年把头蒙在父亲的怀里,嗡声嗡气的说道:“没什么,就是想爸爸了。”
“胡说,早上一起吃的早饭!”
“真的!”对您来说,确实是这样,可是在锦年,已经是五年了!
“真的才有鬼呢。”
“我头疼。”不知道该怎么说,锦年只好发嗲。
贺毅庚抬手摸了摸女儿的头,“好像有点热度。爸爸让柳医生过来一下。”
“不要。大概有点儿感冒了,不看两星期,看了十四天。”贺锦年这会儿只想赖着父亲。
“乱讲。”只是还是退让了,也不在追问女儿了,“到里面休息室里去躺一会。等下若还是不好,就让小柳过来。”
锦年这样也满足了,也不想让父亲担心,听话的跟着父亲进入到休息室。
经历了这些惊心动魄的事情,头又疼得很,贺锦年以为自己一定是睡不着的。可是才躺倒床上没多久,就有些朦胧了,想来这一顿折腾,让她太吃力了。
睡着前,模糊的听到自己手机的铃音。其实这一路上,手机一直在响,可锦年实在是腾不出手,也没有那个心思,就任由响着。贺毅庚倒是怕吵着女儿,找出手机接听了。模糊间,听到父亲说道:“弟妹啊,你找锦年……”
婶婶找自己干什么?只是锦年还来不及多想,终于败给了疲惫,沉沉的睡了过去。
一觉醒来,头倒是不疼了。也不知道现在是几点了,阳光透过休息室高窗上的的五色玻璃照进来,映在对面的红木雕花衣橱上,像是光斑也是五颜六色的。锦年看着那光斑,一时间回不过神来。
贺毅庚的办公室就是个套间,外头是办公的,里头是休息室,中间有扇门。这会儿,这门虚掩着,透了条缝。想来是担心女儿在里头叫人,外头听不见。
套间里静悄悄的,偶尔,只是透过门缝,锦年听着外头父亲笔划在纸上唏唏嗦嗦的声音。蓦然,心慌的很,锦年走到门边,打开门,看着父亲办公。
这点声音已经惊动了贺毅庚,抬首给了女儿一个笑脸,“起来了怎么也不说话?头还疼吗?”
锦年走到父亲跟前,蹲下身,把头搁在父亲的膝上,模糊的说着,“不疼了。就是不想动。”
贺毅庚试了试女儿的温度,好像已经没有热度了。女儿有心事,只是不愿说啊。
“锦年,先头你婶婶打电话来,说你约了她,又放了她鸽子,也不接她电话,小辈可不能这样,等下给婶婶道歉去。”
“哦。我约了婶婶?干什么?”
“你这孩子,昨天晚饭前不是说你们一起去挑WhiteDay的礼物吗?”
锦年只觉得太阳穴突突的跳,好像又要头疼了,WhiteDay,白色情人节!怎么会?“今朝几号啊?”
“你日子真是过昏掉了。今天三月十二号,植树节!”
锦年的头一下子就炸了,五年前的三月十二日!竟然是这一天!就是这一天,她贺四从云端摔了下来,被人直接踩到了泥里头!也就是因为这样,父亲不得不把自己送到了国外。从此,她混混噩噩的,不知道时日的流淌,开始是不能回来,后来是不愿意回来,直到接到了哥哥的那个电话。
“现在几点?”
“四点了,要不,你再歇会儿,等爸爸一起回去?”
就这样睡过去了?那些所有混乱的开端?
即便是这么些年的刻意遗忘,她也没有忘记,薛依婷冲着自己一撇嘴角,然后满脸无措惊呼着倒下去,她也没有忘记,甄柏满脸失望的对自己说,“你怎么能这样?”然后就急奔了过去,只留给自己一个背影……
边上的人指指点点,她感觉不到,她孤零零的站在自动扶梯顶端,抬着一只手,半伸着的手,姿势像推,又像是拉,只是还来不及完全伸出,好一会儿,才颓然垂下。
甄柏,留给自己最后的一幕,就是那个急忙奔走的背影,离自己越来越远,再也没有回头看自己一眼。
那五年的最后半年,自己一直在问自己,真的值得吗?
原来,自己醒来的时候在隆裕广场,就是要去邂逅这些,然后,接下来,王品萱,自己的密友,会给自己电话,赶来安慰自己,再然后……
贺锦年的手贴上自己的小腹,人止不住地颤抖。
“锦年,锦年,你怎么了?”
“刚刚起来有点冷~~”
“这么大了还不会照顾自己!”说话间,一件披肩落在了锦年肩头,贺毅庚按了通话钮,让秘书送杯热茶进来。
赖着父亲,锦年懒懒的不想动,一会会儿,再一会会儿就好。
一年级:星梦奶茶
作文网专稿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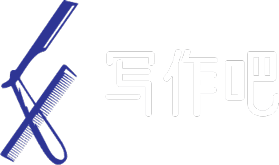
暂无评论
发表评论 我再想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