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祖母走的那一晚,我就睡在她的旁边。妈妈突然摧我起来,给我穿好衣服就抱我走了,她不让我多说一句话,我也被妈妈异常严肃的表情吓坏了,我向床边望了望,只留下父亲跪倒在床边那稍显庄穆的背影映在我的脑海。来不及多说一句话,多看她一眼,一个生命就从我的生活中抽走。死亡第一次以如此近距离的逼近那薄如蝉翼的童年。
印象里,她是一个满脸沟壑、一鬓白发的老太太。她给我一块饼干,我就喊她一声“太太”,这样她就会高兴的笑起来,笑得一脸皱纹,笑得露出仅剩几颗牙齿的牙床,笑得发出奇怪的声音,笑得如今的我满脸的泪来……
小时候,只要太太生病,一家人只有我比较兴奋,因为这样小姨大姑们总要买些“补品”看望她,其中就有我最爱的水果罐头和蜜饯。每当这时,妈妈总以严厉的目光示意我离去,我极不情愿的挪步,眼睛依旧直勾勾地盯着桌上的食品。人潮散去后,曾祖母就用一种怪异的声调喊着我的乳名,我屁颠屁颠地应声跑过去,知道水果罐头和蜜饯在等着我。一次,我问她:“你为什么不吃呢?”她也只是说这些太甜,不喜欢吃。而我,依旧心安理得、依旧狼吞虎咽,而她,依旧那样亲昵温暖的抱着我,看着我吃东西时有趣的模样……
不知为什么对如此细枝末节的生活片断念念不忘,如此深刻。也许只是童年时候的一抬头,她的一抹笑,她安抚我时那亲声的细语,如此温婉、直接。
曾在路上,望见一个过桥的老人,由于身体年迈拄着拐杖在桥边踟躇,无法抗拒她那类似曾祖母的面容,径直走过去亲掺她过桥,不顾众人眼光,一步一步,踏踏实实,那一刻,我感觉曾祖母又回到了我的身边。
过桥以后,她给我一脸沟壑的笑,仿佛是来自天堂的瞩光,让我又看见了她,感触她在我生命中真实的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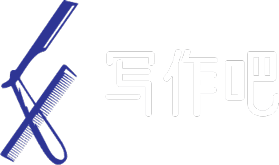
暂无评论
发表评论 我再想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