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周末又去了外婆家,几只鸡在外婆家门前屙鸡屎。我踢了几脚,喊:“去,去……”。
那些鸡便一边大大惊小怪地扑扇着翅膀跑,一边梗着脖子“咕咕……”地叫。然后走开两步去屙屎了。那些鸡长得很威武,可惜没有外婆家的鸡壮实,外婆家的鸡不算很干净,可也说不上脏。毕竟是在乡下,外婆外公老了,退休了。他们又比较疼爱几个孙子,那些鸡也就顾不上喽。
那些母鸡比较爱干净,它们时不时地梳理自己的羽毛,把脑前那团毛弄得白白松松的,公鸡比较脏,懒。为了争偶,乒乒乓乓打上一架,沾了泥水也顾不得了。母鸡总是蹲着咯咯咯地下蛋,而公鸡生性好动,爱跑来跑去。挨着鸡舍墙边的柴堆是它们的最爱待的地方。
它们在上面转啊转啊,寻找虫子的遗迹。于是总是会发生有趣的一幕:一只不明真相的公鸡在柴堆上找虫子,被人发现了,人追着公鸡打,公鸡乱窜乱逃,可总还是被人抓住,丢进鸡舍里。
在夕阳里逃出来鸡舍站在柴堆上的公鸡,总是分外神采奕奕:那鲜红灿亮的鸡冠,红得像正要烧起来的火焰,并不那么炽热,却很鲜亮。那对小小的鸡眼,一身金黄的毛,唯独它挺起来的胸脯是雪白的,全身散发着威严与傲气。可惜好景不长,不一会儿就威风扫把,像打败仗的士兵被人赶回鸡舍,可不过多久,又旧事重演。
扣开外婆家的柴扉,向外婆喊:“外婆好!”便轻轻踏进外婆家的小院。外公外婆都是农民,即便退休了也还是种着几分薄田。外公外婆那一代人苦,出生在社会动荡的年代,小时候没有肉吃,菜里连油水都没有,刚只能勉强吃饱,早早地随父母劳动,分担家事。他们奋斗了一生,才换来眼前安逸的晚年生活。
这小院里只摆了几盆植物,堆了个柴堆,再无更多装饰,却自有一种简洁的美。因是冬天,小院里几棵植物都光秃秃,除了一棵桔子树挂着小小的,胖嘟嘟的,令人喜爱的小红桔子。进门时,外公正在院里择菜。外公一年四季都种菜芯,吃不完就拿去卖,也尽可卖得个好价钱,而那些鸡的主要食物,就是比较老的菜叶。
外婆在厨房里忙活,虽然家里早已有了煤气灶,但外婆还是坚持使用柴火炉灶。问外婆时,外婆就昂然回答:“柴火炉煲出的汤香”。的确,用柴火慢炖,能促进食材本身的味道慢慢融入汤中,使其味道浓郁,萦唇齿之间而久久不散。一锅好的老火汤,汤色清亮,香气四溢。再者,守在一个小火炉旁,看着那明亮的火苗欢快地舔着锅底,这本身就让人心醉。此时外婆正焖着一锅羊肉,羊肉咕嘟嘟翻滚着,让人垂涎三尺!我小孩心性,不耐无聊,便出了院门嬉闹。
门前有块空地,长满了杂草,闲来无事,我就到地里捉捉蚂蚱喂鸡,亦或是把草捣碎了涂着玩,亦或拔一把杂草假装自己在开垦田地,玩累了便去屋里歇着。此时羊肉已闷好了,我抓了一块来嚼。端详着这间老屋,它确实称得上老屋,墙壁上都有了细小的裂缝,却冬暖夏凉。
它很大,很空旷,平时却只有两个老人住。母亲童年时全家住在一间小小的老屋子里,后来外公攒够了钱请人来盖了一间小洋楼,这便是这间老屋的来历,如今它和外公外婆一样快要退休了。从前一楼是两个老人的住处,二楼是我父母的住处,三楼是阳台。
一进屋子见到的就是客厅,虽然老旧家具大都置换过了,可这间屋子的装潢还是老式的,混杂着中式与西式西洋格调,接着便是寝室,在我幼年时常在这里睡觉。来到二楼,这里的风格与一楼格格不入,迎面便是工具台,上面摆满了各种机械和电子设备上的小零件,这是因为父亲年轻时喜爱捣鼓这些小玩意儿,接着又是寝室和一个杂物间。而三楼的阳台则只有几盆小花,几个晾衣架和一个储物间,外婆平时会在这里晒制传统的广式腊味。后来父亲带着我和母亲搬到了城里,这二楼便空出来不用了,沉思间午饭已准备好了。
外婆外公一生生了三个女儿,三个女儿长大了,各自嫁人生儿育女,排行老三的便是母亲。此时一大家人围坐桌子旁其乐融融地享受午餐,十菜一汤,相当美味,吃完饭我便和表弟玩耍。话说我母亲三姐妹生儿育女,却又偏偏生下的都是男孩。
表哥没来吃饭,我自然只能和小表弟玩了,玩了一会儿,大家都要散了,父亲惦记着工作,母亲则想回家大扫除,总之是各有各的理由。外公外婆给每个女儿都准备了大包新鲜的蔬菜,给外孙准备了些小零食,又给了好些土特产,他们尽了两个老人所能表达到的极限去关怀儿女,又担心儿女病了,儿女生活拮据,儿女有什么难处,尽管每个周末我们都会去探望他们……
终于到了离别的时候,两个老人佝偻着身躯向我们挥手,我的心里一股心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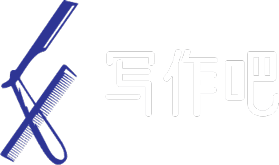
暂无评论
发表评论 我再想想